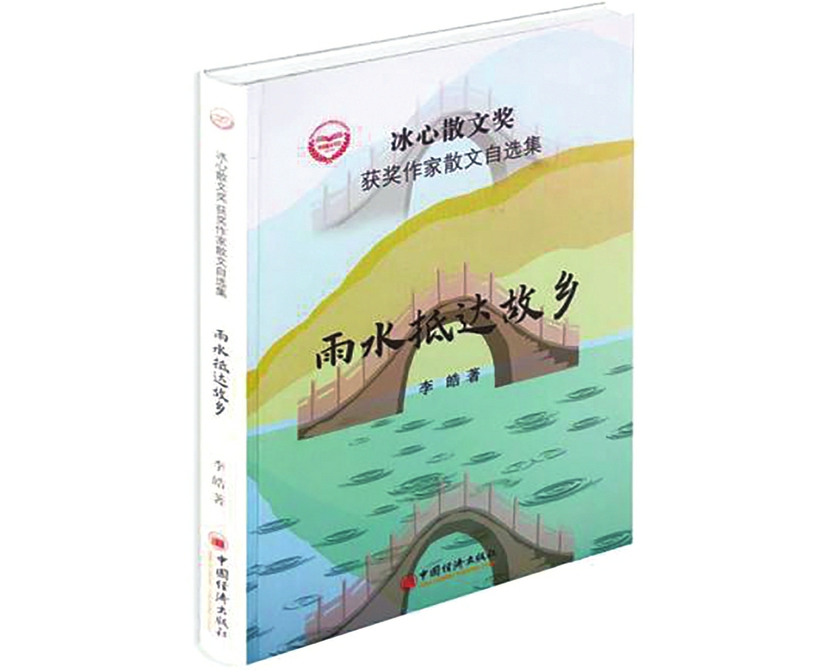《雨水抵達故鄉》
作者 李皓
出版社 中國經濟出版社
生活,總是當下、過去和未來三個維度的共時。走過的路,經歷的日子,常常隱秘地參與現時生活。回味生活的背影,淘洗時光里的質感,浮現某些細節或畫面,是人生之所需,也是散文寫作的重要選項之一。問題在于,日常生活題材的散文寫作要避免對往事追憶的同質化,警惕無深度的講述,而要寫出自己個性化的體驗,提供可以思索的“日常詩性”,并與當下生活共生溫暖之意。李皓散文集《雨水抵達故鄉》中的“故鄉”,不再是地理上的概念,而是過往生活的心靈印跡和情感意象。由此,他的散文是在撿拾和打磨那些有意味的歲月印痕和生活碎片,尋找生活本身的詩性價值和書寫意義。
李皓一直在追求散文的有情書寫,在散淡之中營建共情。散文集《雨水抵達故鄉》分為“煙云生花”“遇見人間”“嘆息橋上”和“碎影流光”四輯,連綴了李皓的個人生活史,勾勒了他人生的行走軌跡和心路歷程。他出生于遼寧大連的小山村,當過兵,做過電業工人、機關秘書、編輯記者,是一位頗有成績的詩人。豐富的生活閱歷,成為他的寫作資源。對日常生活的真情觀照,則讓他回到生活內部去感知。撫摸生活的紋理,吹皺記憶的水面,在飽含深情又從容敘述中追求自己的文學氣質。
生于鄉村,長于鄉村,鄉村自然是李皓重要的書寫場域。以成年人的視角回望自己成長期中的人和事,這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。在散文寫作中,這樣的回望式寫作,底色和表情常常都是鄉愁。與遺忘,與現實,與當下的生活,這樣的寫作常常又是對抗性的。李皓并不如此,而是轉身尋找人生之路上的一個個路標,擦亮內心深處的記憶,品味那些“曾經”之于生命的意義。在具體寫作中,他又將這樣的“品味”還原于平實的細節和場景之中,進行原生性敘述。他將寫作者的身份轉換成引導者,以文字的方式引導讀者進入生活現場,直觀和感受生活。我們在閱讀時,經常會看到一個叫李皓的孩子在一群鄉村孩子之中。而寫作者李皓也會和這個李皓孩子進行些許的對話,偶爾還點評點評鄉村的人和事。點到為止,淡定又節制。其實不僅在鄉村,在所有的過往中,他一直在場。這時候,作家李皓也是讀者,自己逝去生活的讀者。他似乎不是在寫作,也不是在回憶,而是與生活對話,與身后的歲月交流。兩個“我”同時在場,但不處于分裂狀態,也非出于技巧性的書寫選擇,而是以“有我之境”表達對生活的尊重。
以個性化的視角實實在在地寫,注重密度和質感,一切的寫作技巧都隱于其里,不事張揚。作為詩人,李皓區分了兩種文體的敘述姿勢,保持其獨立性。在散文寫作中,他講究文字的素樸,一如生活的清新。他拒絕隱喻和象征,注重最為直白的表達,將詩性完全化于無形。如果說他的詩在竭力拓展想象的空間,那么他的散文則在平常之中隱奇崛,堅守生活本真之于散文的濕潤,始終與日常生活保持同構。在《我的大學,我的軍旅,我的詩》一文,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:“在軍校的一次點驗中,學員隊教導員嚴肅而認真地檢查我的每一本書,甚至一頁頁地翻。最后,他認為幾本《海燕》雜志的封面露腿露胳膊,有些傷風敗俗。我反駁道:‘這個可是世界名畫呀,難道你不知道?’教導員開始犯渾:‘我說不行就是不行,我認為這就是黃色讀物。’我辯解:‘這可是公開出版物呀!’教導員仍強行拿走了那幾本《海燕》。”這是一個細節,是人生的一個片斷,完全可能會被歲月淹沒。事實上,教導員早已忘記了這件小事。然而,李皓是無法忘記的,甚至在心底留下了陰影。當事人不同的身份和處境,就這樣左右了真實的存在。所以在30年后軍校聚會時,他遇上已經轉業到地方的教導員,得知其業余時間專注于國畫創作,特別說到“我現在就是當年沒收你的《海燕》雜志的主編。”從30年前的針鋒相對到30年后的平靜如水,一切都已釋懷。李皓重提舊事,更多的是參悟到了人生的某種哲理,但他不明說,任由讀者去悟。他的散文看似很輕,但裹挾其里的厚重,是歲月之于人生的沉淀。
他的散文多是敘事,但人才是他所要關注的。他不是在講自己的故事,而是在想念遇見的那些人。以故事帶出人物,或以人物引出故事,一切都是平常性的描寫,但感恩之心從未離場。在社會層面上,他筆下的多是些小人物,但就他的情感而言,他們都是大人物。我們可以輕易地發現,李皓真切地認為人生之路是由眾多的“他者”引導和鋪就的,一直不敢忘卻。從家人到鄰居,從志趣相投的朋友到同事,這些人被他視為生命中的發光體,一直珍藏于心,共同凝成李皓的精神故鄉。淡淡的憂傷和濃情快意,是美好的。過往的一切,成為過去,又依然與當下生活形影不離。如此轉身性的寫作,是對人生的真誠認知,又切合真情的內在結構。他寫下的是“小我”,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,但又是我們每個人心靈上的紋路。這是他散文的品格,更是他情感的品格。這成為他個性化的散文寫作倫理,也是我們應該加以關注的散文寫作追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