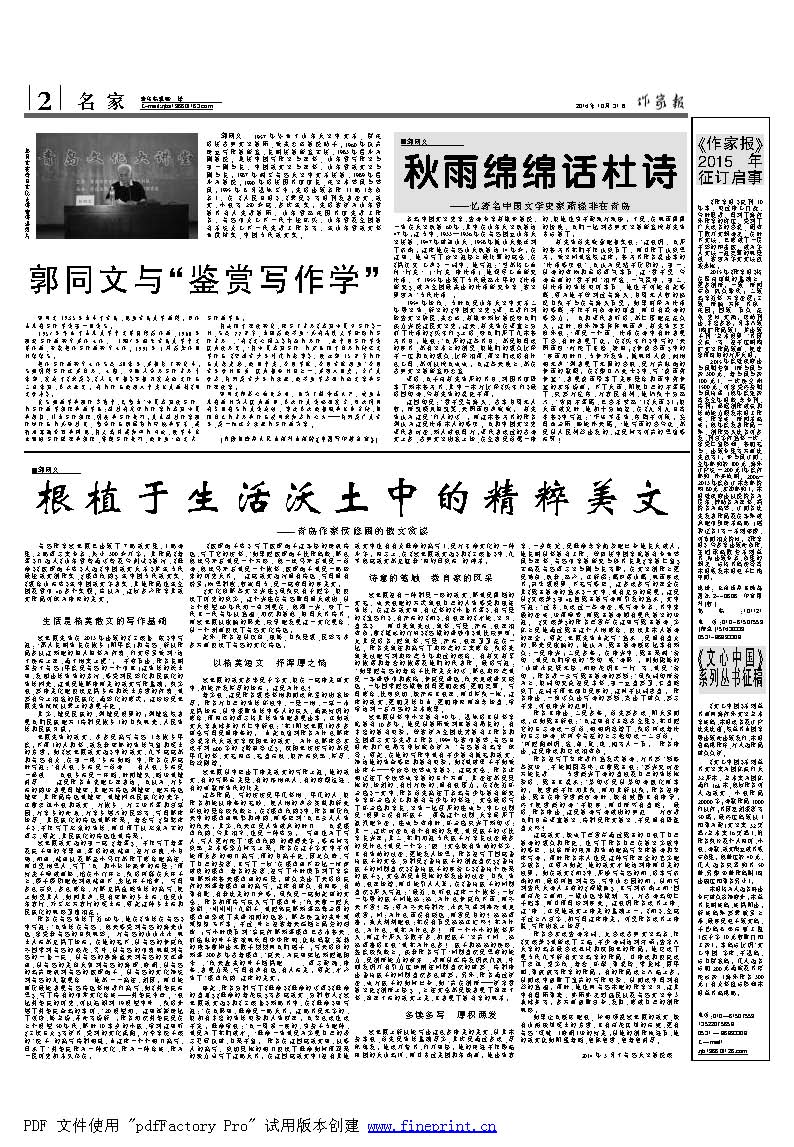
■郭同文
秋雨綿綿話杜詩
——憶著名中國文學史家蕭滌非在青島
著名中國文學史家、唐詩專家蕭滌非教授,一生在大學執教60年,其中在山東大學執教達47年。這當中,1933—1936年在青島國立山東大學任教,1947年重返山大,1958年隨山大搬遷到了濟南。這樣他在青島山大執教達14年余。在這里,他譜寫了治學道路上最壯麗的篇章,在《滿江紅·心聲》一詞中,他寫道:“誓都將心血付‘村夫’”(“村夫”指杜甫),他傾盡心血研究杜甫,于1955年出版了當代最高水平的《杜甫研究》,成為全國最杰出的杜甫研究專家,被學界譽為“當代杜甫”。
1954年深秋,當時我是山東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學生,所學的《中國文學史》課,已進行到隋唐文學階段,黃公諸、蕭滌非兩位教授給我們接力講授這段文學史。這天,蕭先生在課堂上分析了杜甫的《兵車行》之后,給我們開了幾本參考書目。他說:“我開的這些書目,都是值得讀的好書,都有學術上的創見,但他們的觀點注釋不一定和我的觀點、注釋相同,同學們讀后有什么心得,都可以找我談談。我這些天晚上,都在古典文學教研室辦公室……”
課后,我手持蕭先生開的書目,到圖書館借來了兩本參考書,其中一本對注釋《兵車行》最后四句詩,與蕭先生的提法不同。
這四句是:“君不見青海頭,古來白骨無人收。新鬼煩冤舊鬼哭,天陰雨濕聲啾啾。”蕭先生認為這是“行人的話”。而這本參考書的作者則認為這是杜甫本人的感嘆。我和中國文學史課代表討論,兩人誰說得對。課代表讀過的古詩文之多,古典文學功底之深,在全班是首屈一指的,但他也拿不準孰對孰錯。于是,在風雨瀟瀟的傍晚,我們一起到古典文學教研室找蕭先生去請教了。
蕭先生首先欣慰地夸獎說:“這說明,我開的參考書你們不僅認真看了,而且作了認真思考。做學問就應該這樣。參考書作者提出來的‘杜甫感嘆說’,我認為是站不住腳的。第一、從詩的結構和前后語氣來看,這“君不見”與詩前面的‘君不聞’相呼應,一氣貫串。第二、從杜甫的生活經歷來看,他也不可能有此感慨,因為他不曾到過青海頭,白骨無人收的慘況自然不會在青海頭看見。如果解釋為杜甫的感慨,不僅不符合詩的原意,而且有損詩的感染力。”我和課代表聽后,都信服地連連點頭。這時,窗外傳來陣陣風雨聲,蕭先生望望窗外說:“同是一個雨,杜甫在詩中有時表現了喜,有時表現了憂。在《兵車行》中寫的‘天陰雨濕’襯托了悲愁、凄涼;《春夜喜雨》中的‘好雨知時節,當春乃發生。隨風潛入夜,潤物細無聲’則表現了無限的喜悅,是對貴似油的春雨的歌頌。在《贈衛八處士》中,寫‘夜雨剪春韭’,表現夜雨帶來了美好景象和雨中剪春韭的歡樂場面。下了大雨,即使自己的茅屋漏了,只要對莊稼、對農民有利,他仍然十分高興,‘敢辭茅屋漏,已喜禾黍高’(《大雨》);但大雨成災時,他卻十分惱怒,在《九月九日寄岑參》中寫道:‘吁嗟乎蒼生,稼穡不可救。安得誅云師,疇能補天漏。’他寫雨的喜與憂,都是從人民利益出發的,這是何等可貴的思想感情啊!”
